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王迅先生今年已87岁高龄了,他也是“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之父”、两院院士王选的哥哥。和王迅先生打交道的人都有一个最大的感触,那就是他的顶真、直接,有时候甚至不近人情。他的一些学生直到毕业多年后,还会说起在校时“远远看到王迅先生就绕道走”的经历。
但是,和王迅先生交往次数多了就会发现,他“不近人情”的背后是发自内心的温暖和正直。正是他,在评上院士后仍然一直为本科生上基础课。他曾被称为“复旦大学最有名的代课教师”,因为物理系的课如果遇到教授们有急事上不了,就会由王迅代课。因为他的身体力行,物理学系成为全校第一个所有教授都必须为本科生上课的院系。不论是本科生还是青年教师,有人向他求助,他总是来者不拒。连物理学系的本科生看到一些王迅可能感兴趣的文章,也会想着主动寄给他看看。
我大约于1982年底决定在复旦大学物理学系继续研究生学习。当时可供选择的研究方向有两个:表面物理或半导体物理。为确定硕士导师,我咨询了当时的年级辅导员郑国祥老师。听了郑老师对相关导师的介绍后,我的直觉是选王迅老师,主要原因在于:他被排在复旦民间广为流传的谢希德先生的“四大金刚”之首,业务水平在系里是公认的,要想学本领,就得跟水平高的人学。
当然,我也被清楚地“警告”:“他比较清高,不好相处;待人严厉,我们都挺怕他。”过了两天,郑老师在与王老师交流后,交给我一张王老师手写的便条,让我第二天晚上去他家里聊聊。直到现在,我仍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激动心情:被请到家里聊天,这礼遇也太高了吧!
那天晚上是我与王老师的第一次见面。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当然主要是他说我听,他谈到的一个观点是我之前闻所未闻的。他说,我们中国学生都太规矩、太谦虚,不敢挑战老师、不敢挑战权威,而美国学生在教授做报告时,却会不时打断演讲人,提出不懂的问题或给出自己的观点。因此,他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少一点循规蹈矩,多一点闯劲;少一点唯唯诺诺,多一点大胆质疑。用他的原话说,“我们中国学生应该更加aggressive(有攻击性)一点”,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英文单词还可以这样用。
那晚的谈话让我确信,王老师就是我想跟的导师。不久,我们开始填写研究生报考表,报考表面物理的其他同学全都很自然地选择了谢希德先生加上一位副教授作为导师,只有我选择了王迅作为唯一的导师,就这样,我成为了王老师的学生。
他这样引导学生跨入科研之门
全国研究生统考在1983年初的寒假中进行,本科最后一学期的主要工作就是做大学毕业论文。当我去问王老师我应该做什么课题时,他给了我两个选择,要么在刚进口不久的一台大型多功能电子能谱仪上工作,要么在另一台只有一个四极质谱功能的国产设备上工作。
这两台设备的差别,就像一辆崭新的宝马豪车与一辆破旧的平板车之间的差距。
王老师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我听了他半个小时的介绍后,不仅心甘情愿,而且可说是满心欢喜地选择去拉平板车。他说,进口设备当然好,但在这台设备上工作的教师和研究生已经不少,你作为本科生,可能发挥的余地不大,或许只能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而这台国产设备上目前没有任何人工作,虽然功能少一点,但却可以充分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作为一项科研锻炼,不见得比在进口设备上效果差。
之后的事实确实证明,他是完全正确的。
在接下来的四个月中,我几乎每天与这台“平板车”亲密接触,这让我特别享受这种探索的过程,对科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后取得的成果也比我预期的好很多,文章发表在《物理学报》上,这在当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王老师还将我的这项工作,与其他几项在“宝马豪车”上所做的工作一起,投给了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第十七届国际半导体物理学会”,唯独我这项在“平板车”上拉出的工作被大会接受,1984年夏天由王老师在会上报告。
大概在1983年秋,谢希德先生邀请了国际表面物理领域的大家、斯坦福大学的威廉·斯派瑟(William Spicer)教授访问复旦并做系列学术报告。当时,我们系的学术报告已不再翻译了,对我而言就像是听天书。但我坚持全程听完,而且还下定决心:一定要用英语提一个问题。
结果在一个我大概知道他讲什么内容的地方,终于“挤出”一个问题。因为担心提问时出现语法错误被笑话,我还专门把问题写在纸上,等他已经转到下一页讲解时,我才举手打断他。估计当时太紧张了,念的时候肯定是发音不清或是咬字不准,结果他还没听懂,让我再重复一遍,当时我脑子嗡的一下,心跳顿时加速,心想完了。好在我马上镇静下来,把问题重复了一遍,这次他听明白了。有了这次“零的突破”,之后就比较轻松了,我的老师和同学都可证明,我是当年物理学系学术报告会上提问最活跃的那个学生。
在斯派瑟教授访问期间的一个上午,王老师专门安排了一项活动,由我们教研室的教师向他介绍几项我们的工作。完全出乎意料,王老师竟然让我也作为其中一员,用英语向他汇报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工作。
我第一反应是拒绝:我的英语口语,哪有这个水平啊?但王老师说,不少日本人在国际会议上就是完全照稿子念的,你也可以照做。这不明摆着是赶鸭子上架嘛!最后,我还是连滚带爬地应付过去了,当中,斯派瑟教授还不时打断我,向我提问,当然回答就全由王老师代劳了。
如今回想起来,王老师当时这么做,可谓用心良苦,无非是想给我提供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否则他自己去讲,会简单得多,也清楚得多。
“与其到国外让外国人训,不如在这里让我给你做做规矩”
在去过王老师家交流后,有一天,我在物理楼走廊上与他迎面相遇,像对其他熟悉的老师一样,我主动和他打招呼,但他的表情却绝不是我所期待的熟人的感觉,他似乎像没听见似的,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就擦肩而过。接下来的几次相遇,情况完全相似。这时我才有点明白,为什么那么多老师说他清高,因为他根本不屑与别人打招呼啊!逐渐地,我发现这可能就是他的习惯和个性,也许在他看来,这些寒暄都没什么意义。
如果这还不能让人把王老师与“清高”“严厉”“怕他”联系在一起,那么下面我亲历的一件事也许会让王老师的形象“立体”起来。
1985年,我在读了两年硕士后提前攻博,由谢希德先生和王老师共同指导。1987年,谢先生和王老师推荐我去法国同步辐射国家实验室联合培养一年。那时出国算是件大事,何况还是出国一年之久,因此出国前与家人吃个团圆饭,也算是人之常情。
因为知道王老师严厉,我没敢向他请假,而是向教研室副主任林荣富老师请了假,但没想到这竟然闯出了大祸。那天晚上六点半左右,正当我们全家人在杭州欢聚一堂开始举杯之时,突然来了封只有六个字的加急电报“火速返校王迅”!
我的脑袋一下子就炸了,火速骑车到武林门的长途电话大楼,排队半个多小时,才轮到我打电话。能够听出来,王老师说话声音因气愤而有点颤抖:“你读过复旦大学研究生守则吗?” “你知道请假一节课需要谁批准吗?请假半天需要谁批准吗?请假一天需要谁批准吗?”问题劈头盖脸地砸过来。
原来,他就是想说,我这个情况已经需要学校研究生院批准了。凭着多年与王老师的交往,我知道这时的最好反应就是不辩护,否则火力会更猛。等他训斥完后,我说我马上去买火车票,连夜返回上海。
当时,唯一的选择只能是一张绿皮火车的慢车坐票,晚上坐了八个小时慢车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到上海。直奔实验室后,林老师告诉我,原来是法国那边的导师恰巧找我有点事,传真发给了王老师,让他转交给我,这时王老师才知道我回杭州了,于是就有了那份加急电报。
等王老师到了实验室看到我,他没有什么废话,直截了当地说: “与其到国外让外国人训,不如在这里让我给你做做规矩;你现在马上回去写检讨,一式三份,一份交到系里,另外两份分别贴在实验室的三楼和五楼的橱窗里。”当我把检讨书送到系里主管研究生的李白云老师手上时,她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但读过之后便笑着对我说: “你懂的,王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这样讲课不是还可以,我觉得是一塌糊涂”
我在法国期间,与王老师始终保持着通信联系,其间我知道我将会留校工作。当时只要留在专业教研室,基本上就不必从事教学工作了,上课的任务主要由普通物理教研室和理论物理教研室承担。但是,我对讲课情有独钟,因此,我主动向王老师提出,希望回国后的秋季能有机会上《固体物理》这门课,他非常支持。
但按复旦物理学系当时的习惯,上大课前必须要先给主讲老师当助手讲习题课,效果不错才有资格讲大课。为此,王老师与系领导多次沟通未果。最后,他对系领导说: “既然这样,那这门课的任课教师就写王迅和金晓峰,但我是不会去上的。”就这样,1988年9月我给复旦物理学系1985级的学生主讲了《固体物理》大课。
然而,出乎所有人包括我自己意料,王老师从头到尾全程听完了我整个学期的讲课,而且我每次上课结束后,他都会让我去办公室听他对我上课的点评。
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课后,他问我:“你感觉如何?”我说:“我自己觉得还可以。”毕竟第一堂课总是花了大精力去准备的。但让我震惊的是,他说:“不是还可以,我觉得是一塌糊涂。”
接着他一点一点仔细给我剖析,什么地方不行,什么地方不能这样讲,什么地方应该这样讲而不是那样讲等等。所以,我在复旦的第一次上课,就是在王老师这样手把手地耐心指导和帮助下完成的。我原计划在1988年8月进行论文答辩,但备课的工作量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不得已,我只能将答辩时间推迟到了课程全部结束后的1989年2月。因此,可以说,在我的学生生涯正式结束之前,这是王老师给我上的最后一堂无比生动的指导课,其意义远超课程本身而直抵灵魂深处。
(作者为复旦大学物理学系谢希德讲席教授)
本文来源:文汇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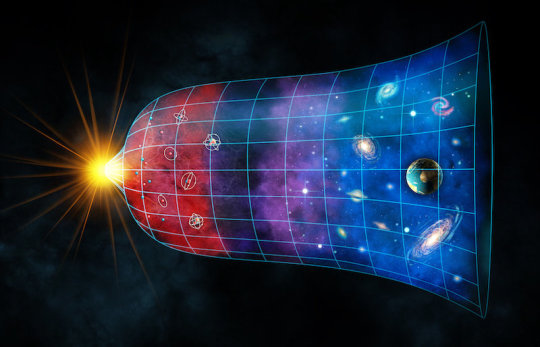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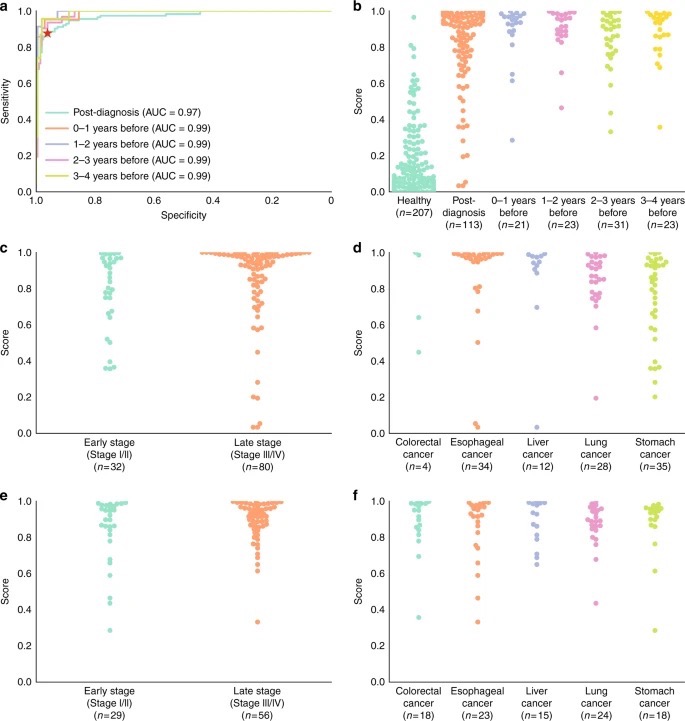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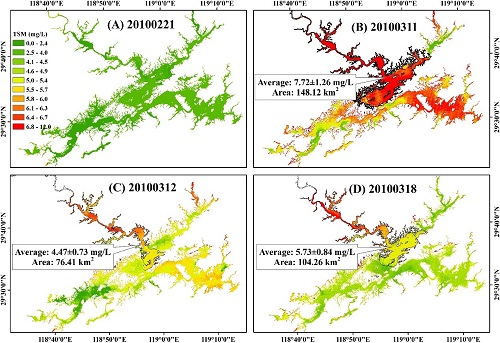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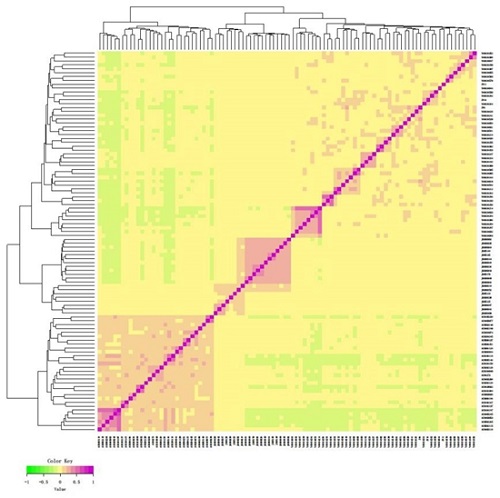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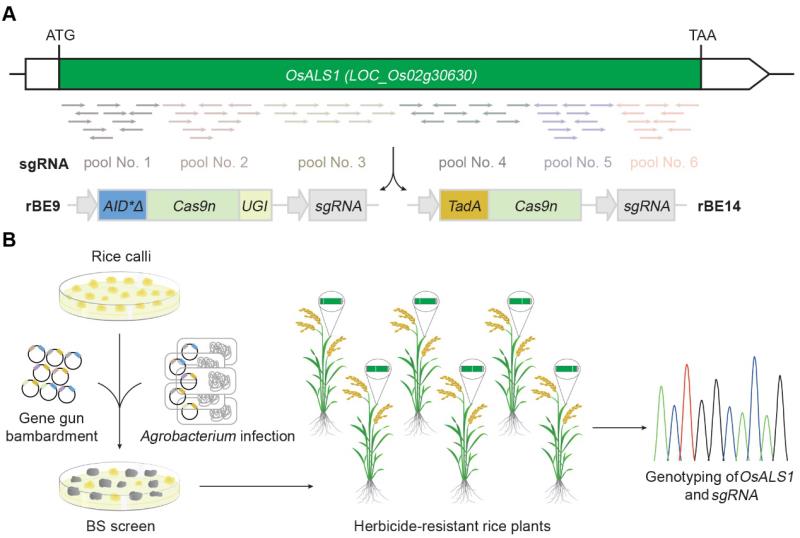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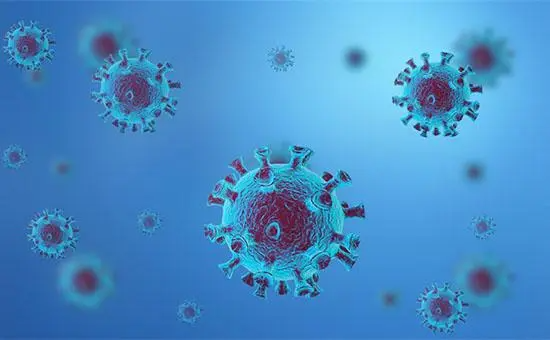








 上一篇
上一篇










